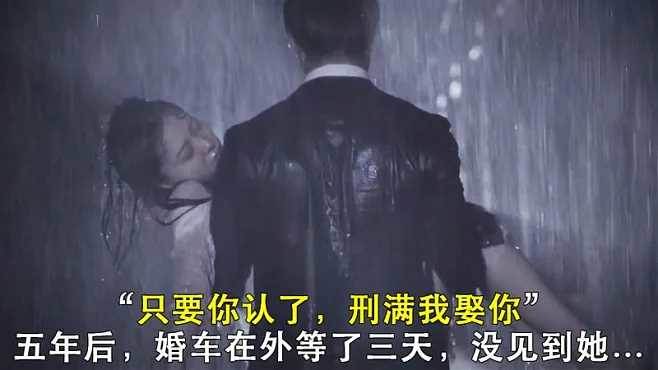《蝕骨危情》第390章
家里的傭人,有些熟面孔,有些生面孔,但無論是誰,見到她時,總是恭敬地點頭示意,而后繞開。
唯有花園里的園丁,她看的不厭其煩。
但這個季節,花木早已枯萎,沒有繁花似錦,更談不上姹紫嫣紅。
扛凍的喬木,還有細碎的綠意。
除此之外,再無一個可以說上話的人……哪怕是動物。
此時此刻,她居然想起那人曾經說過,他寂寞時,唯有與池塘里的魚兒對話。
但……那也不過是謊言罷了。
又去一個星期。
這深庭大院里,依舊,她形單影只。
那人,半月時間過去,卻再也沒有出現在她的面前,偶爾,沈二回來一趟,也不過是拿了一些換洗衣服,匆匆來匆匆去。
除了無盡的迷茫之外,沈三和沈四的臉上,漸漸多了凝重。
她著實猜不出,這二人為何如此。
隆冬這一天,沈家宅院漆黑的鐵藝大門再一次敞開,遠遠的,她從二樓看到,那輛熟悉的賓利車,行駛進來。
便看著那車,發起了呆。
他……到底還是回來了。
收回了視線,她又不知該如何面對那人。
時間點點滴滴過去,管家在門外恭敬地請她下樓。
她想說,可不可以不去見那人。
管家卻已經轉身,疏離的離開。
拖延了又拖延,她還是下了樓。
只心里自嘲……何時起,她已經學會了,識時務者為俊杰。
自嘲的輕笑一聲,笑容來不及綻放,已經隱匿在她日漸消瘦的臉頰上。
樓梯口,一道高大筆挺的身影,靜靜地立著。
是那人。
那人就站在那里,微微仰著下巴,靜靜地看著樓梯口的她。
此一刻,便生出一種怪誕的感覺,那人仿佛一副靜置的畫卷,靜靜站在畫里,畫里的人,正靜靜看著她。
沈二依舊恭敬如斯地站在那人身后,像個永遠的保衛者。
那人看了她一會兒,伸了手出來,朝樓上的她,招了招:“過來。”
屬于那人特有的低沉的聲音,卻多了一絲少見的柔和。
她沉默,又知,躲不過。
舉步而下。
仿佛一個世紀,她有心拖延,她以為那人向來脾氣不好,耐心不足,必然幾番催促,可他卻出乎她的預料,靜靜地立在樓梯口,靜靜地目光迎接她宛如蝸牛的走向他。
莫名的,這一刻,有一種錯覺,好似,那人已經等了她一個多世紀,漫長悠遠,化作松石,依舊挺拔地等著,就為了,等到她。
不過是剛起了這荒誕的想法,她便在心中立即打消掉……又天真了不是。
更何況……她已不知,與他如何再面對面,再如何自處。
一個世紀有多悠遠,她不知道,但她終于走到他的面前的時候,腳下已經虛浮,靜靜地,她站在他的面前,她不敢抬頭去看,卻依舊能夠感受到,來自頭頂溫柔的目光。
或許出于好奇,或許是她腦子抽了,悄然抬眼,偷偷看一眼,便……再也無法挪開。
被他那眼中豐富復雜的情感深深攫住。
溫柔的,繾綣的,眷戀的,還有……還有什麼呢?
她不斷的在心里翻開曾經學到的詞匯,想要從那些詞匯中,找出一個來……可,她翻遍了記憶庫,依舊找不出一個能夠與之符合的字眼。
她的眼中,漸漸浮上了迷惑。
這人的眼神,她不懂了。
覺得眼熟,似曾相識,又覺得陌生,從未見過。
一只溫熱的手掌,便那樣措不及防下,沒有與她打過一聲招呼,輕輕落在了她的額角。
輕輕的摩挲著她那再也去不掉的傷疤。
“當時,很痛吧。”
那人溫柔的問。
她便被這溫柔惹惱,伸手毫不客氣地揮開,“不痛。”她身經百煉,比這更痛的都經歷過了。
問她痛不痛……裝什麼好人吶。
那時,她這麼想著。
那人的手背上,立即浮上一抹紅腫。
沈二怒目,那人卻揮了揮手:“你們都去外面。”
沈二不甘不愿的離開,與此同時,家中的傭人,在管家的帶領下,一并退到了院子外。
一時之間,偌大的客廳,只有她和他。
那人伸手揉了揉自己紅腫的手背,似寵溺:
“無妨。”
她卻不知,該怎麼去打破這詭異的沉默。
那人的聲音,再一次的響起:
“我還記得你十八歲的生日宴上,那時你的模樣,張揚舞爪,肆意得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我還記得那時候的你,像個小老虎,齜牙咧嘴露出剛剛冒頭的虎牙……還挺有趣。”
“我不記得了。”
她便偏要跟他唱反調。
“我記得,是一個夏日的午后,我在樹下閉目休息,你以為我睡著了,偷親了我。”
“我不記得。”她矢口否認。
那人聞言,也只是一笑而過。
“我記得,情人節的一天,你學別的女生,做了巧克力,偷偷塞到我書包里。”
“最后喂了狗。”
男人渾厚的笑聲,蕩漾開,顯然被她逗笑:“沒有,你做的巧克力,我家的狗都嫌棄。”
“對對,你一向嫌棄我。”不知不覺,她被他帶偏,沒好氣的附和道。
“不,最后我吃了。”男人臉上的笑容收了收,眼底一絲認真,卻依舊含笑:
“然后我急性腸胃炎掛了三天水,拉了三天肚子。”
“……”還有這樣的事情?
她想冷嘲,諷刺他滿口胡鄒,記憶力卻有著這麼一件事,她去沈家,沈家的下人說,他們家少爺吃壞肚子住院了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